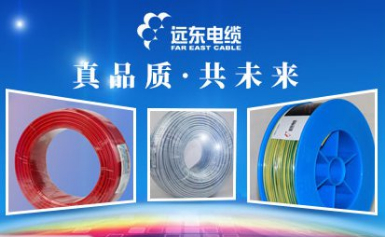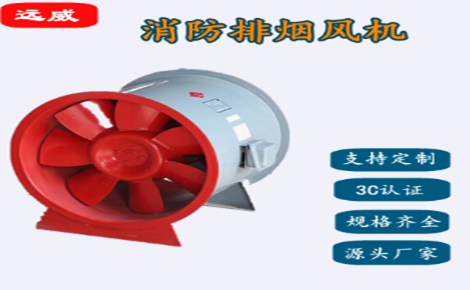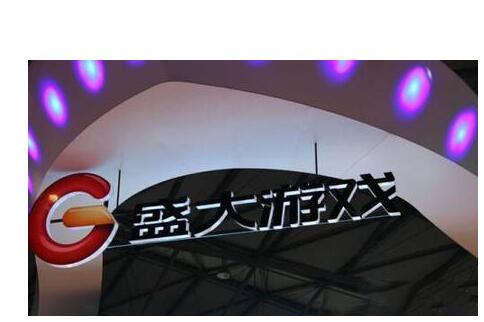與明星面對面
稱葉錦添為東方色彩大家,在圈內外毫無爭議。從一舉獲得奧斯卡比較佳美術設計和英國影藝學院比較佳服裝設計兩項大獎的《臥虎藏龍》,到一路火爆的《橘子紅了》《大明宮詞》《射雕英雄傳》《無極》《夜宴》《赤壁》,再到正在拍攝的《紅樓夢》,這一長串影視作品的背后,都有葉錦添的貢獻。
今晚東藝歌劇廳即將上演的“上海圣翎·演出季”開幕大戲,正是葉錦添與吳興國合作的舞臺劇《樓蘭女》。葉錦添笑著告訴記者,在他的視覺藝術生涯中,《樓蘭女》具有特殊的意義。
跟著哥哥畫畫攝影
葉錦添是一位神奇的東方色彩大家,他的藝術領域早已超出人們熟悉的影視界限。從傳統戲到現代舞,從攝影到雕塑,從廣告、服飾設計到文學創作,他不斷爆發驚人的藝術能量。他的藝術承襲了講求意境的中國文化傳統,以充滿創意,繁復、夸張、華麗的表達方式,向世人展示一種富有東方詩意的超凡世界。
在那么多的色彩中,葉錦添偏愛黑色。“因為黑色永遠安靜,永遠以"遠"的方式存在,黑色可以留在記憶中思考。”站在現今成功的高度,葉錦添回望來時的成長之路,頗多感慨。
1957年,葉錦添出生在香港一個窮苦家庭。“那時真是一無所有,晚上一家六口只能擠在雙層木板床上進入夢鄉。”回憶童年,葉錦添的臉上仍帶著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來的。童年時我沒有發表意見的習慣,只是喜歡想象,個性比較自閉,和別的孩子不太一樣。”
跟著哥哥,葉錦添開始畫畫和攝影。“攝影于我而言,是對世界上一些東西的反映,而繪畫就是在找自己的感覺。攝影讓我學會"看",我將眼睛所接觸到的事物捕捉下來,在沒有任何目的的狀態下,吸收了許多直接的感受;繪畫則相反,它是一種重新的完成,不論看到或感到什么,都必須經過"重新"的過程。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思考,對我后來的創作,形成了很大影響。”葉錦添這樣說道。
徐克領進電影圈
父母擔心兒子會走上窮畫家的人生之路,堅決反對他畫畫。為此,葉錦添和父母爆發了長達幾個月的沖突,直到他后來站在奧斯卡領獎臺上,他與父母的矛盾糾結才算消除。作為妥協,葉錦添考入香港理工學院攝影專業,畢業后去了電影雙周刊《曝光人物》當攝影師。
比較早注意到葉錦添才華的人,是香港電影“怪才”徐克。1986年,吳宇森籌拍電影《英雄本色》,徐克是這部戲的監制。徐克偶然看到葉錦添的一幅畫,對他產生了強烈興趣。在徐克的力薦下,不到而立之年的葉錦添成了該片的執行美術。
回憶當年徐克對他的提攜,葉錦添至今心懷感恩。是徐克的青睞,帶他走進了電影圈,并使他真正喜歡上電影藝術。葉錦添稱他與徐克的感情就像父子:“我喜歡他電影節奏上的天馬行空,他喜歡我空間感上的天馬行空,但我倆的做事風格并不一樣。”
出于對西方藝術的喜愛,1987年,30歲的葉錦添背起行囊,憑著一口不流利的英語走遍整個歐洲。從比較西邊的葡萄牙到東南邊的希臘愛琴海,再到東北邊的南斯拉夫,途徑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西班牙、奧地利等國,他白天吃著面包趕到博物館、美術館,晚上則落腳小旅館和青年旅社。
《誘僧》拿到首個大獎
回來以后,葉錦添滿懷希望,準備在電影上大顯身手,誰知“機會屈指可數,生活窮困潦倒”。雖然他設計了《胭脂扣》《人在紐約》的服裝,還在羅卓瑤執導的《一碗茶》《秋月》中做過美術指導,但命運弄人,日子仍窮得丁當響,甚至一年里沒一部戲可拍,有時連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藝術是什么?葉錦添進入了事業的低谷期,心情郁悶。
就在這個時期,葉錦添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段時間我很瘋狂,到處找老雜志和舊書,有本明報雜志介紹四大名旦,我很著迷。于是我重新看京劇臉譜,看京劇裝扮,看京劇戲服甩袖,為什么這樣甩,這樣跳,發現很多東西你很難用歷史來講。”
葉錦添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電影《誘僧》剃光了影星陳沖的眉和發,反倒成就了葉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個大獎———臺灣金馬獎比較佳美術設計獎。葉錦添說,這是他事業的重要轉折點。
艷麗妖嬈的《誘僧》使他結識了該片男主演吳興國。葉錦添信手拈來的幾幅設計圖被吳興國一眼瞧中:“不錯嘛,愿不愿意跟我去臺灣?”由此葉錦添加盟吳興國孜孜經營的當代傳奇劇場。舞臺讓葉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盡致的宣泄,驚艷至今的《樓蘭女》就此誕生了。
“比較純粹比較瘋”的創作
葉錦添至今還記得,當年那幫意氣風發、只為藝術的人是如何打造《樓蘭女》的。雖然那時的他,口袋里連買一杯咖啡的錢都沒有,還是每天與吳興國興致勃勃地商討如何通過服裝表現一個超現實舞臺。葉錦添把自己關在小公寓樓里,一待就是3個月。在每天踩動縫紉機時,他的頭腦里總會迸發出一些視覺奇觀和獨特符號。
“這些戲服,極盡繁復又華美艷麗,全是我一針一線做出來的。鳳冠代表婚禮、假花代表死亡、鏈條代表枷鎖、利劍象征復仇、海藻意喻生殖,劇情每一步發展和人物內心的活動變化,我都盡量用這些服裝的符號外化出來。1993年《樓蘭女》在臺灣首演,一炮打響,很多年輕人都來了,連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來看我們在搞什么新的東西。”
葉錦添說,當他第一次看到演員穿著他設計的衣服在舞臺上表演的時候,他被震住了。“吳興國讓我懂得舞臺演員身上的魔力。演員可以將你想象的感覺找出來,他們身上有一種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這個力量,你就能讓他演的形象立起來。《樓蘭女》的服裝設計使我在臺灣紅起來,并引起國際關注。可以說,吳興國對我藝術的成功影響比較大。”
葉錦添稱,《樓蘭女》是他當年“比較純粹比較瘋”的一次創作。“在臺灣,喜歡的人把大門向我敞開,不喜歡的人就罵我繁復,但我人生的轉折絕對是從這出戲開始的。”此后,葉錦添好運不斷,先后參與了30多部舞臺作品的設計,為劇場藝術開拓了不少新的可能。
享受不一樣的人生
事業上如魚得水的葉錦添,因為成功變得更自信了。他笑言:“我現在會享受工作的樂趣了,在藝術上也會嘗試很多新的可能。對我來講,重要的是新想法,對生活的看法,而且要快樂。文化發展到今天,人們給予藝術形式以更多的寬容,這讓我、張藝謀、陳凱歌這類美學系統下面的人,有了更廣闊的空間。”
談到眾說紛紜的新版《紅樓夢》人物造型,處于爭議漩渦中心的葉錦添很坦然:“《紅樓夢》是個大題目,李少紅是個很勇敢的導演,有膽量,不管多難的事,她都要嘗試,頂著壓力拼命做出來。她喜歡不斷創新,這一點我們很像,我也不是一輩子只做某種東西的人,而是一輩子逃不出某種東西的人。所以,我總是責無旁貸地給她鼓勁。”
葉錦添指出:“電視劇不應該是守舊庸俗的。我10年前與李少紅合作《橘子紅了》《大明宮詞》時更夸張,所以,我并不覺得現在的觀眾不接受。當然,我也很理解1987版《紅樓夢》對于內地觀眾來說,是感情很深的一個戲,等于是他們年輕時代的一個記憶。但我也希望網友能理解我的感覺,現在畢竟是2008年了,我不能做相同的東西,抱著一種形式不放,這樣可能會有另外一批人對我不滿。”
葉錦添表示,無論是榮譽還是責難,今后仍會有很多,但他不會為之所動,因為游走于服裝設計、視覺藝術、電影美術、當代藝術創作的他,想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比如我現在很喜歡寫東西,寫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藝術工作,讓我有很多積累,我會一本本把它寫出來。我想,這不是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點樂趣來,盡量享受不一樣的人生。”
 2013-06-28
2013-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