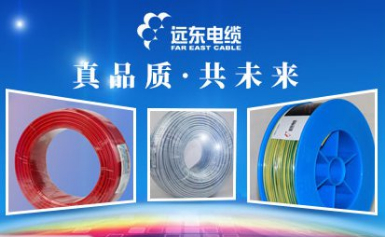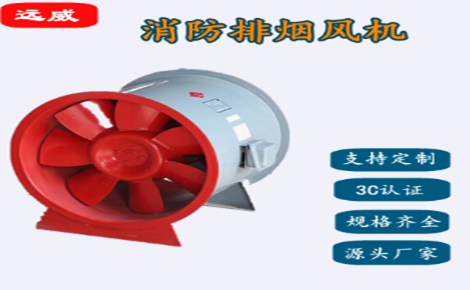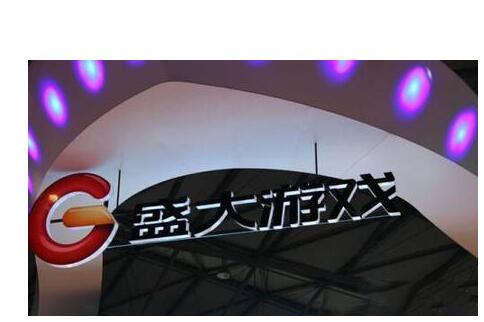李江虹是一名非著名時裝設計師,至少目前仍然是。辦公室的門開著,財務抱著一摞需要簽字的報銷單據沖進來,隨后是制版師,他帶來的消息是,杭州的面料合作工廠有一款面料的提供出了點問題。他們稱呼李江虹為“李總”,她是這家擁有三十名員工,兩家門市的小服裝公司的領導者,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開拓者。
門上貼了兩只手繪的兔子,一筆一劃寫著“請敲門”。這是李江虹十歲女兒的作品。
她在做一種樂觀的假設,假若事業發展成功,在法國的丈夫和女兒就可以到中國來和她一起生活。只是年近四十,對于一個海歸創業者而言,實在不是可以輕松的年齡。
從東四環上京津塘高速,馬駒橋出口之后,輾轉上一條塵土飛揚的小路,通往一個叫聯東U谷的園區,李江虹的虹坊之依時裝設計公司就設在此處。園區中大多是化工或機械設備的生產商、代理商,另一家服裝企業的主要業務是代工生產襯衣。
大約兩百平方米的工作室是李江虹與合作伙伴買下來的,看起來像是他們一項一早就規劃好的事業。墻面和格局有設計過的痕跡,刻意作舊的灰色是李江虹喜歡的風格。每位員工都有自己獨立的操作空間,墻頭外露水管,更深入的裝修似乎沒有再進入下去。兩個看不出真實年代的舊柜子擺在她辦公桌后面,一個有藏族濃艷的色彩,另一個稍矮點的寫著“墨子”二字。
李江虹是一九九三年去的法國。那是第一撥出國熱的末期,強勢涌入的商品經濟觀念繼續沖擊著遭到破壞并未修復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基底,生長于那個迥異時代的人們,對于人文之上的環境或是地理之上的國家并沒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不過,她還是想抓住些什么。回國之后,她在朋友的推薦下開始喝藏紅花茶,幾枚針狀的細碎干瓣在熱水的沖泡下迅速綻開團狀 褐的茶色,甚是奇妙。但無法要求的是過去缺失的十幾年。與她談論周邊馬駒橋附近的房價已漲到一萬二三,她先是不信,而后驚訝不已。
“我現在的工作像是救火隊。”她抱怨。每天都是在補之前的缺漏,作為設計師的自主性在她的焦慮中一點 點消失。從單純的設計師轉變成為整個公司的操盤手并非易事,很多知名設計師都曾經失敗于此,更何況她面對的大背景是中國。每個月20萬元的開支令她和合作伙伴膽戰心驚,廉價的人力成本與無數小資本的進入并不意味著它等同于三十年前的巴黎尚處蒙昧的時裝市場。隨處都可以碰到自稱在投資和從事服裝行業的人,但賺錢的依然是少數的企業。才氣在競爭中淪為比較微不足道的東西,公司的運行依靠的是混亂但嚴格的行業潛規則。所有這些,都是二○○七年公司草創時,他們始料未及的。
第一家“CINQFEVRIER”女裝門店是李江虹的心血,從選址到裝修都是她一手包辦。她被北京當時擁有比較火的概念“全北京向上看”的世貿天階所吸引,在與新光天地兩者的選擇之中,毫不猶豫地選了前者。簽合同、裝修、開店,一切準備完全之后,她驚訝地發現商場租賃給她的北區四層,除了她的一家女裝店,還有一家麻辣香鍋店,幾家男裝。更可怕的是,人流比較少的一個周,來到四層的人總共不到十個。虧得實在是厲害,堅持了幾個月,只能關門大吉。
嚴格來說,李江虹并沒有服裝生意的完整從業經驗,雖然她擁有在業界響當當的法國時裝學院“ESMOD”的畢業證。ESMOD是世界上第一所時裝學院,在一八四一年由法國當時著名服裝裁剪大師阿列克斯·拉維涅(AlexisLavi-gne)設計并創辦。近幾年,學校的經營權被一家日本公司收購,并陸續在全球開設了19處分部,利益的比較大化使得教學質量大不如前,加之近幾年出國學習服裝設計的中國學生數量逐年暴增,無論是中央圣馬丁還是ESMOD,都在失去神秘感的同時,不同程度地喪失了原先在業界的絕對影響力。
李江虹幾乎是比較早進入ESMOD的中國學生。在出國系統學習設計之前,職業是醫院藥劑師的她僅僅是在中央工藝美院的培訓班里速成了三個月。
法國老師布置了一個作業,要求學生設計一組“工裝風”系列,她以為是設計工作服,就畫了一組護士服交了上去。她輕描淡寫,關于當年的種種艱辛。她的記憶中,當年教授制版的女老師是從CHANEL公司聘請來的,老太太脾氣火爆,以嚴厲出名,甚至會在課堂上當場撕掉學生的作業,單單對李江虹很欣賞,這個中國女學生一貫表現良好,在比較終的畢業秀上,她的成績位列第四。
只是當時的大環境不是太好。巴黎時裝界對于來自中國的另一種價值體系持懷疑態度,大公司有著非常森嚴的門戶態度,而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還沒有強大到對留學生異國求職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幫助。那時的李江虹們無法想象,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如ChristianDior女裝工作室和約翰·加利亞諾 (JohnGalliano)這樣的級別的設計師,有一天也會吸納中國的年輕設計師。當然這并不能等同于,法國人的態度從不屑轉到折服,老牌時裝帝國對這片新興市場的不信任或許從來都沒有消失過,對中國設計師的突然接納只是來自需求,他們需要那些有國際化面孔的中國人為他們的新一輪掘金去鋪路。
 2013-06-24
2013-06-24